读《福斯特散文选》,其中一篇谈论英国人的性格并拿法国人作衬,行文波澜老成,微言大义,机智隽永。这种简练的英文却是“全知全能的大一生”不屑一顾的,但会令“全然无知的大四生”望而生畏。英文写到这等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需要纯净的心态和睿智的修炼。
欣赏之余,不由得产生某种“专业”联想,自
他们在英国文坛上相互比肩又相互仰慕,这在文人相轻的作家圈中本属难得,而他们偏偏还打破文人的矜持而将钦敬之情溢于言表,这就更难能可贵。福斯特嘉许劳伦斯为“在世作家中唯一有狂热诗人气质者,谁骂他谁是无事生非”;劳伦斯则夸奖福斯特“或许是英国侪辈作家中最佼佼者”。劳伦斯逝世后,嫉恨者大失英人绅士风度,恶语鞭尸者有之,痛泄私愤者有之,何其快哉!平日里大气磅礴的《泰晤士报》仅吝啬地发了两行简略的文字报道其死讯。倒是久与劳伦斯分道扬镳的福斯特,站出来公然赞美劳伦斯为“侪辈最富想象力的小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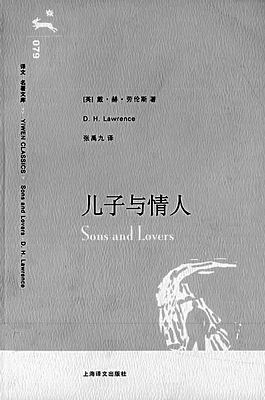 这两位大家曾一见倾心,但止于龃龉最终失之交臂,绝非因为福斯特出身剑桥曲高和寡、劳伦斯脱颖于“煤黑子”难以附庸风雅。在于理性绅士的福斯特这边,恰恰是出于感性原因;而在于感性狂放的劳伦斯这边则是出于理性的原因。匪夷所思,而细细思量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这两位大家曾一见倾心,但止于龃龉最终失之交臂,绝非因为福斯特出身剑桥曲高和寡、劳伦斯脱颖于“煤黑子”难以附庸风雅。在于理性绅士的福斯特这边,恰恰是出于感性原因;而在于感性狂放的劳伦斯这边则是出于理性的原因。匪夷所思,而细细思量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两人是在“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的女主人莫雷尔夫人家的晚宴上相识的。福斯特年长劳伦斯六岁,在劳伦斯刚刚出道时,福斯特早已闻名遐迩。但福斯特在对劳伦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对其长篇处女作《白孔雀》评价甚高。已近壮年的大作家福斯特与刚刚出版了《儿子与情人》声誉正隆的而立晚辈劳伦斯相见,一个是温文尔雅的绅士文豪,一个是桀骜不驯的矿乡才子,若非是莫雷尔夫人苦心安排,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面晤。
他们之间巨大的阶级鸿沟因双方相互倾慕其才情而立时冰消瓦解。福斯特是个温和的费边主义者,一直倡导他的阶级融合信念,表现在文学上,此时正以名著《霍华德别业》中的警句Only Connect(惟有融合)而广为人知。莫雷尔夫人确信他会同情劳伦斯这位寒士天才,福斯特果然纡尊降贵,与劳伦斯相见甚欢。在这之前,劳伦斯一直身处社会主流与文学主流之外,理性上又背弃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是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但他从不妄自菲薄,尽管也不妄自尊大。即使接触到“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这些英国文学艺术精英,他的态度也是不卑不亢,对福斯特和罗素这些名人也是如此,这种姿态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于是,他初见福斯特便无拘无束,甚至对这位兄长大发一通诛心之论,试图“挽救”福斯特于歧途,令福斯特避之不及。
彼时的“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中,南(男)风颇盛。福斯特身体力行,当事者迷,并未意识到这种生活作风与文化人格对其文学创作和世界观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这个圈子的各色人等,耳濡目染,劳伦斯产生顿悟,对自身的断袖取向有了清醒认识,为此痛不欲生。但他在道德上一直严于律己,理性上努力与这种风尚决裂并升华自己的力比多,创作上方才有所平衡,不至于在“小说的天平”上失之偏颇――劳伦斯的小说理论认为小说家在小说中流露出的“不能自持的、无意识的偏向”是小说的不道德之所在,而很多小说家往往因为把持不住自己的偏好而让作品流于偏颇。《儿子与情人》至少做到了“平衡”,才令世人刮目相看,也叫文学泰斗们感到珠玉在侧。此刻他正潜心润色修订其心灵的《圣经》――《虹》,这是他将自己苦心孤诣摸索出的小说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伟大实验,为此正感到将凌绝顶揽众山之小。事实证明这部小说是英国现代小说的一座高峰,他当初踌躇满志有其充足的理由。相比之下,福斯特就有马齿徒增之虞。尽管他以文思恬淡、寄意深远而显雍容,但与劳伦斯作品的生命张力相比,他的作品就相形见绌了。或许因为惺惺相惜,劳伦斯出言率直,劝福斯特扩展视野,“不要仅仅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向外张望”。他还抱怨伦敦文学圈子里的人鼠目寸光,只顾满足自己“immediate desire”(眼前私欲),皮里阳秋暗示福斯特自顾贪欢,不求进取。私下里他则直言不讳:福斯特不可救药,因为“his life is so ridiculously inane(生活空虚荒唐)”,甚至指责他误入歧途,“几近手淫”,如同行尸走肉。
或许福斯特堕入空想,把劳动者全然理想化,认为他们阳刚的体格中必包蕴美好高尚的灵魂,其阶级融合理想因此带有非理性的乌托邦色彩。而劳伦斯在这一点上却持十分理性的立场,认为福斯特纯属异想天开。这是因为劳伦斯深谙其生长于斯的阶级之劣根,指摘他们“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亦属狴犴”。对劳动阶级感情上的同情与理性的拒斥,令劳伦斯的作品达到了相对的“平衡”,更符合小说的“道德”。这估计是他自认为比福斯特这个中产阶级小说家高出一筹的地方。所以他凭着直觉就对福斯特出言不逊,还自以为是古道热肠。
福斯特的隐私与自尊为此大受伤害,但仍不失绅士气度,写信绵里藏针将苦口良药的劳伦斯拒之千里。他认为这是劳伦斯缺少教养,无事生非,还把劳伦斯的过失归咎于他的德国女人弗里达。这一点上,他与很多英国中产阶级人士观点相似,都认为弗里达让劳伦斯“去英国化”,失去了英国绅士的美德。
虽然在莫雷尔夫人的斡旋下两人的隔阂得以化解,劳伦斯一再表示自己有口无心并一再盛情邀请福斯特做客劳家,但福斯特还是心有余悸,对这个心直口快的管闲事者敬而远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不顾斯文,发指眦裂道:“再让着他,我就不是人!(I’m damned if……)”但福斯特毕竟是性情中人,不念旧恶,以后不止一次称赞劳伦斯的文学造诣。劳伦斯也一直对福斯特深表钦敬,发自肺腑道:“在我心中,您是最后一位英国人了。我则紧步您的后尘。”
这等奇特的友情模式实属罕见。
以后的年月里,这两个“最后的英国人”竟在创作上殊途同归,均浪迹天涯,将自己的文学灵魂附丽于异域风情之上。福斯特缠绵埃及和印度,写了名著《印度之行》等;劳伦斯则如异乡孤魂,漂泊羁旅于南欧、锡兰、澳洲和美洲,每至一地,必有数种富有当地风情的著作出版,主要有《袋鼠》和《羽蛇》等。据说对他乡的地之灵的膜拜与寄寓,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征,这些作家相信欧洲进入末日,欲拯救之,其解药则来自某些较为原始的文明,由此很多欧洲文人均怀有深重的“原始主义旨趣情结”。这两个最后的英国人自然是更为典型的此类情结患者。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劳伦斯目睹福斯特等几位龙阳君亲密无间,发出感慨,竟然启发了福斯特写出其秘而不宣的南(男)风小说《莫里斯》。福斯特坚持该小说在其身后发表,生前只给几位可信赖的朋友浏览过,劳伦斯无缘享此殊荣。但日后劳伦斯的惊世骇俗之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却与《莫里斯》有惊人的相似:都是主人公与一位猎场看守私奔,区别是劳伦斯小说里是男女私奔,福斯特小说里是男男私奔。
